


3月27日,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对话中发表了最新的观点:
"当AI真的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水平,它一定能极大提高全球生产率,或许能让发达国家重回10%的GDP增速。而且这一次可能和工业革命不同,并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或'北半球'受益,因为技术扩散会非常快,全世界各地都能同时接触到这些能力。"
这番言论立即引发了科技和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毕竟,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曾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却往往伴随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工业革命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但也将世界划分为受益的"北半球"与被遗忘的"南半球";互联网时代同样如此,数字鸿沟让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而纳德拉的预测意味着,AI革命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一历史模式。10%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经济规模每7年翻一番——远超过当前大多数国家1-3%的增长率。更令人兴奋的是,纳德拉认为这种增长将是普惠全球的,不再重蹈工业革命时代的覆辙。
主持人: Satya,非常高兴你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不确定你还记不记得,5 年前我们举办年度大会,庆祝我们的 25 周年纪念时就邀请过你。当时在活动开始前两周,世界突然发生了改变——所有事情都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你那时候非常配合,我们就用虚拟方式进行了访谈,那次对话也非常精彩。谢谢你当时的配合。我今天特别兴奋,终于能现场和你面对面交流。
Satya Nadella: 我也同样高兴能和你现场见面。
主持人: 回顾 11 年前,你成为微软 CEO 时,也许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西雅图会诞生两家加起来市值超过 5 万亿美元的企业——一家是微软,一家是亚马逊。只是看微软这 11 年间所取得的成绩,你接手时公司市值大约是 3000 亿美元,如今则接近 3 万亿美元,实在是令人瞩目。老实说,当年我自己都没法想象会是这样。我也常常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成长?我先把时间拨回到 11 年前。当你决定接过微软 CEO 这个担子时,你当时有哪些想法或期望?你觉得那时候会发生哪些事情?然后,能否谈谈你在过去 10 年里担任 CEO 的过程中经历的一些关键转折点?
Satya Nadella: 首先,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来这里,也祝贺 Madrona 的 30 周年。我最近也在想微软即将到来的 50 周年,这真是难以置信。昨天我还在想,当年微软成立时我才 7 岁,而如今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2014 年我成为 CEO 时,我脑中其实就几个很简单的想法。那时我清楚自己是第一位“非创始人”CEO——当然,你可以说 Steve(指 Steve Ballmer)并不是公司“正式”的联合创始人,但他在公司仍享有创始人一般的地位。我是在一家公司里成长起来的,这家公司是由 比尔·盖茨和 Steve 打造的。所以,作为“非创始人”,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创始人所做的那些事——也就是“给公司注入使命感与远景”——再次成为我们的核心。这能赋予我们道义上的正当性,也能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公司为什么而存在,该如何发展。我觉得当时我们需要再次回到根基上去想想。在 1975 年,Paul 和 Bill 创办微软时,他们对于软件的设想其实超前于时代——当时“软件行业”几乎还不存在,但他们提出“我们要创造软件,让别人也能基于此创造更多软件,并由此催生一个软件产业”。这就是微软最初的构想。如果在 1975 年这个概念能成立,那么在 2014 年它依旧是正确的,在 2025 年它甚至更加重要。
因此我重新回到微软的初衷,从中汲取灵感,把它提炼成我们今天的使命——“赋能地球上每一人、每一组织,帮助他们取得更多成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家“没有在位创始人”的公司,我还想将“文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通常在由创始人领导的企业里,文化常常是“隐含的”,因为很多东西是创始人的特质或他们的“个人魅力”自然而然带来的。但对我而言,我没法依赖这种隐含的创始人文化,所以我决定让文化变得“显式”,加以塑造。我当时很幸运,接触到了 Carol Dweck 的“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理论,并把它引入公司。说真的,这个概念之所以对微软内部如此有效,并不是大家把它当作“新 CEO 的新口号”,而是它直击人性的某些本质,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感同身受。所以,重新确立“使命”、把“文化”摆在首位,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两件事。当然,这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还是得制订正确的战略,做好执行,并且能不断自我调整。但是,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使命感和文化,你连尝试的机会都不会有。过去 11 年,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一框架。
主持人: 我记得你是在那一年的 2 月份正式接任 CEO,然后到了 2014 年 5 月,你对外的第一个重大宣告就是“我们要让 Office 跨平台”。对很多了解微软文化或曾身处微软生态的人来说,这一声明具有非常强的冲击力。这是不是你有意要告诉外部,也告诉公司内部:“这就是我们的新策略”,或者“这代表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
Satya Nadella: 其实,早期的微软就是跨平台的:我们在 Windows 还没发布之前就先做了 Mac 上的 Office。后来我们在 90 年代取得巨大成功,所以公司内部逐渐就变成一种“只有 Windows 才是最重要的”氛围,但那其实并不是微软最初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是“做软件并希望软件能无处不在”。不过也不是我在 2 月一上任就说“赶紧做跨平台”了。Steve(当时的 CEO)在任时其实就批准了这方面的方向。只是这个举措恰好在我任上对外宣布,也解锁了微软在云时代应有的价值主张。回头看,如果当时上帝让我在“移动”和“云”两者里只能选一个,我会选“云”,并不是说移动不重要,而是云的生命力也许会比客户端设备更持久。当时我们在移动领域的地位也比较尴尬,只能算第三名,而我深知在这样的生态中“第三名”的处境非常艰难。所以我们必须在云上努力做到稳固的第二名(在当时),并逐步扩大在 Office 365 和 Azure 上的优势。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各类软件和终端就必须出现在各种平台上。那次发布会,其实就是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主持人: 你之前谈到要“让文化发生转变”,并且强调“成长型思维”。如果在场有人还没读过 Carol Dweck 的那本《心态:新成功心理学》,我强烈推荐你们去读,真的是关于文化和个人成长最好的书之一。我自己每天都在努力践行,但还在不断学习。我也常听你讲,要从“什么都自以为懂”转变为“努力去学习”的文化。但毕竟当你上任时,微软已经有十几万员工,大家有自己的工作模式与思维惯性。想要在这么大的组织里推行文化变革,过程究竟有多容易或多困难?
Satya Nadella: 成长型思维”的价值在于,它不是号召“宣称自己拥有成长型思维”,而是要求我们去面对自己身上的“固定型思维”。实际上,你一旦声称自己“完全拥有成长型思维”,那就意味着你并没有真正的成长型思维。这个概念有点“递归”在里面。做起来确实不容易,需要从领导者自身开始。比如,大公司里常有人谈“冒风险”,可真正的潜台词却是希望“别人”去冒风险;或者说“我们要改变”,但又觉得是“别人”需要改变。所以要真正改变一个组织,必须先改变自己,这很难。但“成长型思维”给了我们一个工具,引导我们努力去直面自己的“固定思维”。在微软内部推动这种文化,一开始就得高层与基层同时行动,而非单向自上而下。另一点就是要有耐心。不能今天早上说“我们从现在起都得有成长型思维”,然后到晚上就要看到结果。你要允许各级领导者带着自己的热情和故事慢慢地把这个概念融入团队。
幸运的是,这个概念非常“有机”,它让人们感觉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更好的人,很多人打心底认可它。我们也在执行层面“放松管控”,例如我们没有设定文化转型的硬性指标,也没有搞那种“KPI 红黄绿”,这样也避免了“游戏化”或形式主义。当然,它也会被滥用。偶尔我也会看到会议中有人指着别人说:“他们都没有成长型思维”,而不是先反思自己。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且永远不会“完成”。你没法说“好了,我们文化转变成功了”。事实上,尤其在当下,AI 带来了新一轮冲击,我们又得重新学习很多东西。
主持人: 在聊 AI 之前,先说点和你个人兴趣有关的话题。你在高中、大学都打过板球,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起工作的趣事之一,我们也在尝试让板球通过MLC(职业板球大联盟)在美国普及。你多次提到,板球这项运动给你的思考方式、领导风格以及人生都带来了积极影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Satya Nadella: Caitlyn 和我在一起工作,每次我在社交平台上发跟板球相关的内容,就能收获来自印度的海量点赞。她总是说:“天啊,你怎么不在发微软产品内容时也获得这么多点赞?”但这确实是因为印度有十几亿板球迷啊。其实,所有团队运动都会带给人很多启示,尤其是对组织文化或个人成长而言。举个例子:竞争精神。有次我在球场上看到对面有个澳大利亚球员,实力超群。我当时站在前置守备位置,看他挥杆简直目瞪口呆。这时教练(我们称之为“Physical Director”)冲我们喊:“去竞争,而不是只会崇拜。”在场上你必须全力以赴,拼尽全力,而这也是体育教会我们的——不惧对手、全力竞争。
团队合作。我记得有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我们队里有个非常棒的球员,但他对队长有意见,就故意不接一个球,让对手得分。结果我们 11 个人的士气瞬间跌到谷底,既生气又觉得被背叛了。那次经历让我认识到,如果你的明星队员因为与领导闹别扭而故意破坏团队,那对团队是多大的伤害。领导力。还有一次,我是投球手,当时投得很差,队长就把我换下来,自己上场投球并拿到一个三振,但随后他又把球换给我继续投。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需要你一整个赛季的发挥,而不只是这一场比赛,所以我得确保你的信心别被打没了。”我当时心想,一个高中队长就有如此高瞻远瞩的领导力,也太令人钦佩了。这就是团队领导力的精髓:要让团队里每个人都发挥好,而且是持续地发挥。所以,团队运动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以及在球场上学到的那些“血淋淋”的教训,我到现在都很受用。
主持人: 让我们聊聊 AI。就像你刚提到的,在微软的历史里,可能经历过几波平台浪潮:先是客户机-服务器,接着是互联网和移动,然后是云,如今则是 AI。其实微软在 AI 方面已经投资了很多年,并不是一两年才开始的。你能分享一下,为什么微软在自身大力投入 AI 的同时,又要和 OpenAI 进行战略合作?这段合作关系从起初到现在经历了哪些演变?今后又会走向何方呢?
Satya Nadella: 说得没错。微软大概从 1995 年就开始在 MSR(微软研究院)里做机器学习(ML)研究,例如语音识别之类,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和 OpenAI 的合作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最早合作时,他们在用强化学习(RL)做 Dota 2 的研究,那会儿他们专注于强化学习,这并不是我们当时特别关注的领域,所以只是浅度了解。后来,当他们决定要用 Transformers 技术攻克自然语言时,我们就决定“下注”。老实说,这正是 OpenAI 的高明之处,他们敢于把所有筹码都押在“扩展规模(scaling laws)”这件事上。我读到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由 Ilya 和 Dario 撰写的“scaling laws”相关内容,说只要加大计算规模,就能让 Transformer 模型的表现随之提升。
自然语言一直是微软非常关注的领域。Bill对自然语言的痴迷由来已久,他曾设想要把所有的“人、地点、事物”都编入某种数据库,然后用 SQL 去查询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笑)。这是微软早期对 AI 的想法。我们最初以为只要在这种结构化世界上再加点语义层就够了。但 OpenAI 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思路:直接用大规模的神经网络和海量数据去逼近语言本身。一开始我们也说不准,直到我看到他们用 CodeX 模型(GPT-3.5 的先驱版本)做代码自动补全,这真让我震惊。因为写代码的工程师是最挑剔的一群人,他们从没想过 AI 能让编码变得轻松。但事实就是这样——AI 确实可以极大提升编程效率。那一刻我才真正相信了“scaling laws”在实际应用中能发挥巨大价值。于是我们就加大了对 OpenAI 的投入。这之后,我们看到诸如 GitHub Copilot 等产品不断进化。我们在过去 3 年里让代码补全功能越来越强大,最近又发布了新版本;与此同时,Chat 模式也同步在变强,可以进行多文件编辑;还有能读取整个项目库的智能代理;在 Azure 里也有类似“Copilot for Azure”的东西。从“AI 配对程序员”到“AI 伙伴程序员”,演进很快。
主持人: 我记得在 GitHub Copilot 还没正式公测前,我们一起吃过饭。当时你花了二三十分钟给我描述 GitHub 那边正在做的“Copilot”,我当时想:“他真的非常激动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你对一件事表现得如此兴奋。后来产品公测后,我才体会到它的影响力。那么在这个早期阶段,你是怎么在公司内部推动这个项目的?毕竟任何大公司对新鲜事物都会有些阻力,尤其是这种可能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
Satya Nadella: 关于 Copilot,其实可以说有两个关键时刻。一个是 Copilot 自己的诞生,另一个是 ChatGPT 的出现。ChatGPT 其实一开始谁都没料到它会成为一个“产品”,最多觉得是个“采集数据”的实验demo。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它一下子就火了。对微软来说,正是有了之前构建 Copilot 的经验和基础,当 ChatGPT 出来后,我们就能迅速把它的能力“复制粘贴”到所有微软产品里。我回顾过去几波浪潮,往往就是这样:Windows 3.0 出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如何在后续版本上加速发力。如今在 AI 这波浪潮里,我认为我们是走在前面的,所以也能在从 GitHub 到 Office、从 Azure 到 Bing 的各条产品线上快速落地。当然这仍然是早期阶段。在你后台和我聊天时,我们还说,这就像图形界面出现的早期,或者网页出现的早期。整个行业都在摸索:价值会沉淀在哪个层?是模型层?是基础设施?还是某类应用?这些都有待时间来验证。
主持人: 让我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做风险投资的看法是,AI 堆栈分为“AI 基础设施”、“模型”和“智能应用”三层。以往大多数价值都集中在应用层,不管是横向应用还是垂直行业应用,都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次会有不同吗?
Satya Nadella: 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如果回顾历次技术变革,企业价值主要会在两个地方累积:
1、某种围绕用户体验的“组织层”,比如图形界面之于客户端,或者搜索之于 网络;
2、基础设施层的效率提升,比如数据库、云平台等。
所以,这次也是类似的逻辑。对于我们这样的“超大规模”云厂商来说,AI 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未来对算力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比如深度学习需要虚拟机或容器,这些都要跑在庞大的云基础设施上。像 ChatGPT 之类的应用,还需要数据库来存储所有状态——它现在就是 Cosmos DB 的大用户。而它向我们采购算力时,其实是买下 GPU 或 AI 加速器与存储、计算之间按一定比例配置的整套资源。所以我认为做“超大规模云”是一门好生意,我们只要继续在规模和成本上保持领先即可。至于模型和应用层的价值分配,就没那么明朗了。可能某些消费级场景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在企业市场则会是另一种图景,这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不过我现在最确定的一点,就是世界对计算力的需求会持续猛增。
主持人: 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提到可以从“能否提升 GDP”的角度去衡量 AI 的成功与否。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切入点,能不能再展开讲一下?
Satya Nadella: 之前有人问我如何判断“通用人工智能(AGI)”是否到来,市面上也有各种标杆或说法,但我觉得都不太准确。我的想法是:假设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了上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那么要收回这个投资,就得产生相应的收益,比如一年赚 1000 亿美元利润。那要想真正赚到这 1000 亿,你就得在全社会创造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的经济价值,换言之,你得带动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所以我说,如果真的达到所谓 AGI,它一定能极大提高全球生产率,或许能让发达国家重回 10% 的 GDP 增速,这可能类似某些工业革命高峰期的表现。只有到那个时候,大家才会说:“好吧,这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一次可能和工业革命不同,并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或“北半球”受益,因为技术扩散会非常快,全世界各地都能同时接触到这些能力,我觉得这点非常令人兴奋。
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成果发明人与专利转化者、生产工艺设计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甚至70%的股权,但是好像没看到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的专利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我们应该参考《拜杜法案》,把科研成果的投资者、研发人员转化人员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使用
“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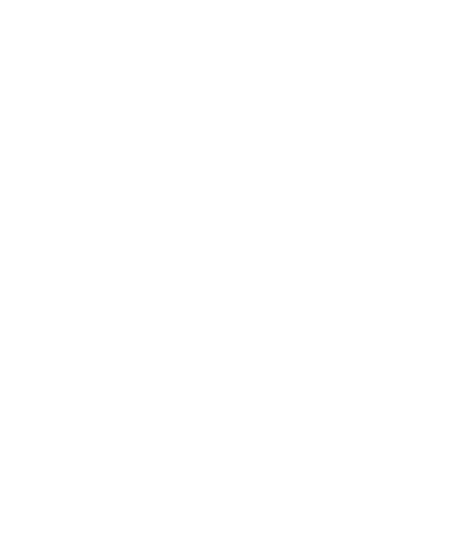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