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机接口(BCI)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话题之一。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士报告厅”,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理事郑海荣,为观众做了一场“脑机接口与生物智能”的演讲,分享了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人工智能的最高形态是生物智能,而脑机接口是生物智能发展的抓手之一。

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更适合医疗应用
“人类大脑就是一个生物的宇宙,我们外面是一个物理的宇宙。如何把生物的宇宙和物理的宇宙连接起来,这是重要的科学命题。”郑海荣说。 近期,国内多个科研团队宣布脑机接口进入临床阶段,能够帮助患者重建肢体运动功能,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全球范围内,马斯克旗下Neuralink公司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推进方面较为领先,已实现脊髓损伤患者完成打字以及玩马里奥赛车等复杂任务。 但在郑海荣看来,此种高歌猛进的脑机接口赛道也需要被重新审视。“脑机接口如果接进去,就有一个挑战。”他解释说,“因为人的大脑已经进化300万年了,你放一根针,把这些电极放进去,它(大脑)会跟你打架的。所以生物相容很难,经常装了几个月,(电极)就根本不导电了,信号也出不来。” 在他看来,即便是创伤更小的介入式方案,其核心思路依然是将人造的传感器“置入”人体。“非要把人的大脑打开,放进去一些芯片?”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蛮力工程”,而非对生命智慧的真正理解,其本质上是把大脑——这个极为复杂的生物体,当成了一台可以随意插拔硬件的机器。 基于这种理念,郑海荣及其团队所倡导和研究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无创”之路。其核心逻辑是,不再试图用物理电极“刺入”或“贴近”神经元去窃听信号,而是通过超声波、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外部物理手段,在不破坏颅骨这层天然屏障的前提下,实现对大脑内部信息的“读取”,甚至是“写入”。 他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士兵”与“粮草”:“大脑里的神经元是前面打仗的士兵,血管就是后面的粮草,血流跟神经活动有高度的关联性。”他认为,通过高分辨率的成像技术去观察“粮草”的动态,再用AI大模型去反推“战况”,就有可能解码大脑的意图。 这已不是天马行空的构想,郑海荣亦在现场介绍了由他牵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正是致力于“用超声波去控制神经元放电”,并已在动物实验中实现了对老鼠记忆和行为的精准调控。
人工智能的最高形态是生物智能
郑海荣之所以对“蛮力工程”提出批判,其根源在于他对人工智能产业未来终局形态的判断。他认为,AI的发展必然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数据智能”,即当前所处的大模型时代,其本质是利用海量数据进行学习和创作。“以前靠人力来掌控这些数据太累、太复杂,”他解释说,“但是计算机让它可感,可以做分析,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很多。” 第二阶段是“物理智能”,即AI与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实体结合,影响物理世界。 第三阶段则是靠脑机接口实现的“生物智能”。他引用了人工智能先驱图灵的论断:“脑与机器的融合并协调工作,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唯一途径。” 在他看来,“生物智能”才是AI的终极形态,也只有这种由人类大脑直接控制的、与生物智慧深度融合的智能,才能真正降服当前AI模型所暴露出的各种隐忧,确保技术始终朝着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当被问及“脑机接口是脑控制机,还是机控制脑?”这个终极问题时,郑海荣表示,“人工智能可能产生强大的威力,如果操作不慎,将对人类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可能的。这也是我倡导发展生物人工智能的原因。因为只有生物控制的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大脑控制的人工智能,才是可以有效降服的。” “未来一定要让‘脑’控制‘机’,而不能让‘机’控制‘脑’。所以大模型的监管规则非常重要,我觉得对这块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郑海荣最后说。

文章来源:院士+,版权属于原作者,本网站仅用于公益宣传,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使用
“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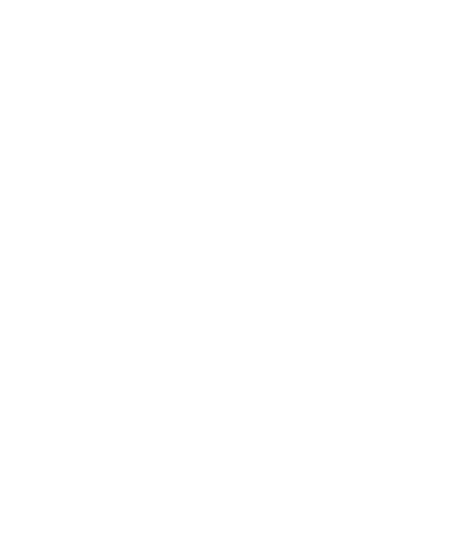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